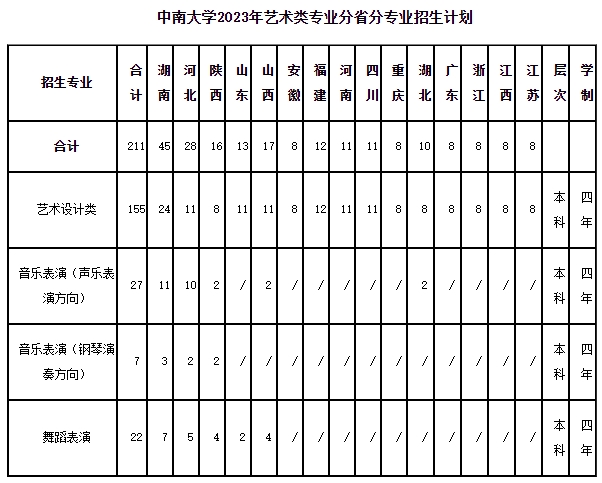1945年以來的西方雕塑(八)
觀念藝術與大地藝術
極少藝術有一些分支,彼此之間有明顯的差別,但實際上又非常接近。其中之一是觀念藝術,它將極少主義轉變到一個完全非材料的地步。藝術變成為觀念的藝術,或為信息的藝術。
觀念藝術的先驅之一是約瑟夫·庫蘇斯(JasephKosuth),他在60年代后期的某些作品就已在最正統的觀念藝術的范圍之內。他以對藝術市場的物質主義懷抱敵意而著稱,他對波普藝術擁有的物質主義利益作出了猛烈的反應。例如,庫蘇斯在他的《作為觀念的藝術》系列中,精心安排的作品包括從使用能在畫廊出售的經過裝裱的直接影印品到在報紙中被預定的版面。他寫道:
這種把作品的直接性強調出來的方式完全可能與被分割的繪畫聯系起來。新的作品與昂貴的物品沒有關系--它和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東西同樣是可以接近的;它不是裝飾性的--與建筑也毫無關系;它可以被帶到家里或博物館,但不是有意為它們而制作的;也可能通過當眾撕毀來處理它--夾到筆記本里或貼在墻上--或者根本不去撕它--但任何這一類的決定都與作品無關。作品一旦與公眾見面,我作為藝術家的作用也就結束了。
另一個以文字為媒介來創作的藝術家是勞倫斯·韋勒(LawrenceWeiner)。在1980年12月我對他的一次訪談中反映出韋勒是以相當特別的方式來看待他的作用的:
我認為按照某種藝術史的分類來看,與你最為接近的應該是雕塑。因為雕塑涉及人類與物品的關系,物品是指與人類相關的物品。人們是采用它自身的非物質的語言來制作它。當你看到一尊雕塑,當你看到一塊地上的木頭,上面又放著一塊石頭的時候,你必須在你的腦海中以某種語言來轉譯它。我試圖做的事情就是表現語言自身,這一有關雕塑是什么的關鍵問題……它是一尊雕塑在語言中的體現。
韋勒用黑色的大寫字母把他的雕塑寫在墻上,從而提供了一種公共場景。但他更感興趣的是在書本中來展現它,正如庫蘇斯在一螺報紙中來展示他的作品一樣。作品本身是用單個的詞--"FOLDED"(對折起來)--或一句話--"ANOBJECTTOSSEDFROMONECOUNTRYTOANOTHER"(一件從一個國家搖擺到另一個國家的物體)組成的。觀念藝術在大地藝術中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孿生兄弟,它和非材質的觀念藝術一樣在物質材料上是開放的。大地藝術能夠(但不必定是)由巨大的挖掘工程和對自然場景的選擇來組成,這些特征不可避免地促使人們將它們與原始人堆砌的古冢和大地作品作比較。在這種類型的大地藝術中兩個最突出的例子可能是邁克爾·海澤(MichaelHeizer)在1969-1970年美國內華達州梅薩的維爾京河上做的《雙重否定》;和羅伯特·史密森(Robertsmithson)在美國猶他州大鹽湖上做的《螺旋形防波堤》。很明顯,兩者都向往某種神秘性和原始性。海澤談到他的巨型雕塑有一種"感應力",但構成它的基本概念既不是社會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純粹的智力。1500英尺長、50英尺寬以及30英尺深的壕溝被藝術家視為一種否定的體積、一種虛無,并涉及在此之前的實有的體積和在開掘搬運過程中獲得的力量。
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盡管是用一種最古老和最普通的象征形式來制作的,但也同樣是個人的創造。螺旋形及其環境都是出自自覺的美學選擇。
這兩件作品在外觀上都是巨大的,而且為它們選擇的地點都是現代藝術的觀眾無法到達的偏遠地區,甚至史密森的不那么大型的作品也是同樣的情況,如《非位置--不明確位置》和《被埋了一部分的木板房》。作品的觀眾不可能在實地來考察它們,它們只是記錄在攝影,或電影和錄像上的東西。把它們與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在規模上看來可能要小得多,現代旅游業就把它們作為金字塔來看待。對于地景藝術來說,有時要在作品本身與它所產生的攝影形象之間作出明確的區分是很困難的。這種困難很明顯地反映在丹尼斯·奧本海姆(DennisOppenheim)的一些作品中。在1969年的《引導播種--麥子》系列中,藝術家在大地上制造出來的富于節奏感的線痕只有借助專業的高空攝影才能被看到和欣賞,而設計本身也是由照相機的高度、角度和方向來決定的。
純粹就規模而言,最雄心勃勃的大地藝術規劃可算是保加利亞藝術家克利斯托(ChristoJavacheff)的作品,其規模甚至超過了海澤。克利斯托于1950年代未在巴黎做的《被包裹起來的物體》造成了最初的影響,很顯然,在哲學觀點上它主要應歸功于杜尚的一些現成品觀念。它們最直接的先驅是杜尚在1916年做的《隱藏的響聲》,這個作品是由兩股繩圍著一個小物件繞成的一個球狀的東西構成的,晃動這個東西就會發出嘎拉嘎拉的噪音。
克利斯托的包裹計劃很快就開始超出室內的規模。1961年他宣布了一個把公共建筑包起來的計劃,1968年他實現了這個計劃,把波恩的藝術博物館包了起來。同年他為第四屆卡塞爾文獻展創造了一個280英尺高的"空氣包裹"。1970年克利斯托在米蘭包裹了德拉·斯卡拉廣場的列奧納多紀念碑,同年在美國進行的一個大型計劃--科羅納多的《峽谷帷幕》使他獲得了廣泛的聲譽。這件作品在其最寬的部位有1368英尺長,最高點高達365英尺。在完成這件作品的四年之后在加利福尼亞做的《奔騰的柵欄》只有8英尺高,但長達24.5英里。在這件作品中,克利斯托用了兩百萬平方英尺的尼龍布,90英里的鋼索和2050根鋼柱,每根鋼柱的直徑達3.5英寸。1983年他又進行了另一個巨大的計劃--做在弗羅里達州大邁阿密的比斯開灣的《被圍起來的島嶼》,需要650萬平方英尺的聚丙烯布來完成這件作品。
與海澤和史密森不一樣,這些作品都只是臨時性的,克利斯托從不追求在風景中留下永恒的印記。盡管它們是在前些年才完成的,但在今天留下的只有克利斯托的素描稿和文獻性的照片,這些素描本身也是極完美的藝術品。(由于必須增加的費用,必須吸收的地方財政資助和地方基金理事會的審議過程)它們也成為一種向公眾宣傳當代藝術精神的有效手段,克利斯托曾認為他將這種宣傳留下來的遺產視為其藝術職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要欣賞英國雕塑家理查德·朗格(RichardLong)作品也必須局限在照片上和在朗格自己的攝影技術的一個實質性范圍中。不過,他是用非常簡單的方法來制作的,攝影的形象并不被作為主要的部分來看待,他認為照片不過描述了這種"事實,對偏遠、荒涼而又不可認識的作品有正確的理解。某些雕塑很少被人看到,但可以被很多人知道。"因此,他接著指出(他自己分的行):
我的戶外雕塑是各種地點。
材料和觀念取決于地點;
雕塑和地點或是同一的。
地點的最遠處是眼睛從雕塑能
看到的
地方。對一件雕塑來說,地點或
是在行走中
發現的。
有些作品是在一條道路上的特殊地點的連續,例如《里程碑》。在這件作品中,行走、地點和石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朗格最有特點的表現形式是在偏遠和荒涼的景色中造成的小交錯;其存在是后來用攝影來證實的。在畫廊里除了展出他的照片之外,朗格還展出其他的記錄形式--例如,標示著特定的行走路線的一張地圖,或對一組行為所作的簡短的文字說明。或者是將文字記述與照片組合在一起的地圖。他也有特別為畫廊制作的雕塑。它們通常是由石頭(有時是木棍和小樹枝)構成在一個特定的地點和置于地板上的一個簡單圖案中。這樣,人們就能在他的作品中發現將勞倫斯·韋勒這樣的觀念藝術家與羅伯特·莫里斯及卡爾·安德列這樣的極少主義藝術家聯結起來的線索。
在朗格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強有力的聯想,但這些聯想不是體現在藝術家正好命名了的那些作品中;這些聯想與暗示解釋了他的感染力,正是這種感染力使得他的觀眾比人們所預料的要多得多。朗格將禪宗佛教的因素,一種在面對自然時的中庸消極的態度,與其他更為傳統的東西綜合到西方藝術中。人們能夠將他與英國特有的園林風景傳統聯系起來--自然被作了微妙的改變,以便與他真正的自我更加接近,也能把他與17世紀以來更加寬泛的阿爾卡迪亞(古代希臘的世外桃園--譯注)風景畫傳統聯系起來。這表明朗格作品的愛好者總是出自都市的白領階層(他對博物館工作人員有一種特殊的感染力)。他們與17世紀的那些最欣賞克洛德·洛蘭及其追隨者的藝術的人是相對應的,朗格取代它們而進入了自然的神秘,在一種替代的形式中喚醒了阿爾卡迪亞式的自由。
不過,在朗格的藝術中有一種特有的當代特征,那即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對象轉移到對制造對象負有責任的人的方式。朗格將他的行為區分為分散的行動或計劃,每一個行動又都是作為藝術品來設計的,而且他本人也成為他自身最完美的產品。他不是唯一的后期現代主義雕塑家--他的搞法可以被這樣稱謂--還有一些以更大的熱情追求同一目標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人杜奧·吉爾伯特(duoGilbert)和喬治(George),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于斯。
在介紹這些藝術家之前,還有一位英國雕塑家的活動值得一提,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與理查德·朗格很類似。尼古拉·玻普(NicholasPope)和朗格一樣對自然的同一性有著浪漫的感情,他通過鑿痕粗糙的雕塑來表達這種感情,如《白拱》,就是盡可能少地改變自然材質。不同之處在于玻普的雕塑雖然在地點上也很荒涼,但是用不同于朗格的方法制作出來的。這不僅在于他的作品有人的參與,而自然實際上也被迫改變為新的形狀,因而與傳統雕塑程序的聯系更為密切,無論多么原始的結果也可能出現。
吉爾伯特和喬治將他們自己稱為"生活雕塑",并宣稱他們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雕塑--日常生活中所有瑣碎的動作;對于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形,他們的解釋非常簡單:"我們從學校畢業了,我們無所事事,沒有畫室。我們就是藝術。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他們最初一舉成名的作品是名為《我們的新雕塑》的一段表演,后來更名為《在拱門的下面》。這個作品首先于1969年在倫敦的兩所藝術學校表演。藝術家穿著正式的禮服(這后來成為他們的商標之一),舞弄著兩件道具,一只手套和一根拐杖。同時一架電唱機奏出音樂廳的歌曲《在拱門的下面》。在后來的表演中增加了一些特點--他們在臉上涂滿厚厚的銅粉,站在桌子上面,下面仍然是電唱機,因此他們模模糊糊地類似于一個與音樂匣組合在一起的自動裝置。
一個非傳統的藝術作品的潮流同時涌現出來--另一種表演、郵政雕塑(由寄給朋友和熟人的明信片組成)、明信片雕塑(通過并置普通商業明信片所構成的設計)、大型草圖(仍可歸類于"雕塑")和照片組合,逐漸流行開來的照片組合在效果上更加精細和更加專業化。在其日趨成熟的形式中,這些作品有時在規模上堪與19世紀學院派藝術家所創作的不可一世的沙龍繪畫相媲美。當吉爾伯特和喬治的藝術繼續具有強烈的自傳性時,他們總是通過照片來組合他們的形象。其情調可以是抒情的或略帶諷刺性的。他們或者是壓抑的,或者又完全是恐嚇的。這些照片組合充滿著各種模棱兩可的含義。它們所暗示的事物都沒有明確地表述出來--在這兒可能是對同性戀的暗示,在那兒又顯然是贊同新法西斯主義,也可能是關于過時的原教旨主義宗教。吉爾伯特和喬治的前衛追隨者顯然不愿意在他們的行為中對其所指作出解釋,藝術家自己保持著冷漠,以適合他們長期以來為自己所選擇的角色。他們所維護的偽裝都體現在這一段話中:"這是使我們感興趣的我們的共同形象。那只說明一件事,我們對它感興趣。它是一種令人驚異的力量。它變得象一個堡壘,比一個人的力量要強大得多。"
就藝術家與藝術事實之間始終維持著一種如此緊密的確證關系而言,吉爾伯特和喬治是一個例外。以同樣的行為開始其藝術生涯的其他前衛藝術家,隨著他們藝術經驗的增長進而制作保留了傳統分類的雕塑。這種變化的例子是美國藝術家布魯斯·瑙曼(BruceNaumen)和德國藝術家瑞貝卡·霍恩(RebeccaHorn)。瑙曼是以其幾段表演而嶄露頭角的,如藝術家在1979年接受加拿大《前衛》雜志記者的采訪時所指出的那樣,這些表演不斷增加對環境的要求,"環境用于對內容的控制,因而也更加重要……如果我能限制所表演事物的類型,那么我就能部分控制經驗。"他的近期作品似乎把環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一個生活表演者的出現就變得不那么必要了。觀眾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進入藝術家所提供的空間,表演起到引導的作用。
瑞貝卡·霍恩生于1944年,只比瑙曼小三歲,卻屬于另一代藝術家。她作為一個藝術家的活動在整體上屬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她最早的"雕塑"是消費品一一面具或手套(這些東西在高度上超過三英尺),雕塑家自己身體的延長。然后進入表演,如《中國未婚妻》,這件作品要求觀眾的合作。他或她被邀請走進一個涂著黑漆的六面體小房間,進去之后,門被突然關上,把觀眾留在一片黑暗之中,這時聽到兩個女孩在用中文對話。
她在最近的裝置作品已是機械性的,但機械裝置卻隱喻著不要求觀眾的參與。如1982年的《孔雀機器》就是放在一個人面體空間的中間,隨著雄孔雀發出的求偶的尖叫聲,一把用金屬制成的長穗扇緩緩張開。這些東西當時都是放在很低的位置上,觸及到房間的四壁,實際上占滿了地板的空間,象征著它的開合。
后期約瑟夫·博伊于斯的雕塑也充滿著隱喻--在這方面他可能是受瑞貝卡·霍恩的啟發。事實上他的雕塑主要集中在隱喻的陳述,它們沒有明確的"風格",也不可能描述一個典型的事例,即使重復采用了某種材料,如肥肉和毛氈。但更為重要的事實在于博伊于斯是以其成熟的藝術生涯作為他自己的藝術作品,就其更完整和更投入的樣式而言,甚至超過了吉爾伯特和喬治。他的很多現在置放在博物館的雕塑不過是"剩余品"--使人從物質上想起博伊于斯在它們的基礎上進行的活動。當然,這些也是他與吉爾伯特和喬治的重要區別--博伊于斯的政治信念表達得更加明確,也更為深刻地把政治信念融合在他的行動作品之中。它們與前衛藝術悠久的左派分離主義傳統的聯系也更為密切。
博伊于斯出生于1921年,歲數大得足以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他首先是作為轟炸機駕駛員在俄國前線服役,戰爭結束時他正在一個臨時拼湊的傘兵部隊參加荷蘭的戰斗,戰后回到了德國。他的戰爭經歷給他留下很深的心理創傷,并總是浮現在他的藝術中:他的飛機墜落在克里米亞一個荒涼的地方,韃靼收人救了他,并照料了他八天,直到德國的偵察部隊把他營救出來。這種瀕于死亡而又奇跡般再生的經歷似乎觸發了他當一名現代巫師的愿望,盡管這種愿望在戰后很長一個時期才萌發出來。
博伊于斯逐步獲得世界聲望的過程和他的藝術一樣是不正規的。戰爭一結束他就學了一段時間的雕塑,隨后在杜塞爾多夫及其他地方初露鋒芒,由于戰爭的創傷和恐懼留下的后遺癥,使他在1957年經歷了一次精神崩潰;他回到家鄉克萊文斯休養了幾個月,干了一些農活,使身體逐漸康復。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他后來說道:"疾病幾乎總是生活中的精神危機,為了接受積極的變化,舊的經驗和思想的各個階段在這種危機中被中斷了。"
1961年,博伊于斯獲得了杜塞爾多夫學院大型雕塑的教授職位。這等于是承認了他日益增長的地位--通過授予前衛藝術的重要人物以這類職位來確認他們的成就,也是德國傳統的一部分。例如,大部分德國重要的表現主義畫家在希特勒迫害他們之前都獲得了重要的教授職位。而且博伊于斯也恰巧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教員,對經歷了長時期的壓制才開始抬頭的德國青年和反叛的一代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杜塞爾多夫學院為他的活動和前衛團體激浪派的成員提供了一個便利的基地,他現在與激浪派關系密切,雖然他不是該團體最初的創始人。激浪派成員對表演和其他偶發的事件感興趣,強烈反對商業性的畫廊制度。
博伊于斯現在開始把他的創造性活動引向一系列表演或"行動"。這些活動建立在一種復雜的材料象征主義之上,其材料涉及到他在戰時與韃靼人相遇時的某些經歷,但更深層的是它們被用來提出有關藝術本質及其與社會的關系等特殊問題。博伊于斯使用毛氈(當他受傷后處于半昏迷狀態時,韃靼人用毛氈把他包起來)、蜂蠟、鐵絲、蜂蜜和黃金。他最聳人聽聞的一種材料是肥肉。博伊于斯的一段話提到他在1964年做的《肥肉椅子》(把一大堆肥肉砌成三角形放在一張普通的木質椅子上):
我最初的目的是用肥肉來激起一場討論。在我看來,材料的靈活性特別依賴于溫度的變化。這種靈活性是心理上的效應--人們從直覺上感到它與內在過程與感覺的關系。我要求討論有關雕塑與文化的替在性問題,它們意指的是什么,涉及什么樣的語言,涉及什么樣的人的產品和創造。因此我在雕塑上采取了一個極端的立場,一種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又與藝術無關的材料。
1967年,為了對急劇變化的德國政治形勢作出反應,致使博伊于斯的生涯第二次改變方向,這種政治形勢特別反映在學生的要求上,他們認為學院應該成為每一個申請者都可以進入的地方,而不在乎他或她是否具有某種資格。他發現他所屬的派別,"作為準政黨的德國學生黨"(GermanStudentPartyasMeta-Party),支持這種要求,這種立場導致他與杜塞爾多夫學院的同事們處于日益激烈的沖突之中,他們指責他是"傲慢的業余政治藝術家"。1972年,博伊于斯領導一個派別占領了學院,以支持學生的要求,結果是他自己被解職了。隨后是一系列沒完沒了的官司,直到1978年才最終達成一個協議,允許博伊于斯保留他的教授頭銜和畫室,但取消了作為大學教員教學的資格。
從那時起,博伊于斯作為一名逍遙派藝術領袖的行為早已推翻了杜塞爾多夫學院試圖強加于他的種種限制。他成為戰后德國前衛藝術集團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他的德國學生黨已轉變和擴大為"通過公民投票爭取直接民主組織"。
在1972年的卡塞爾文獻展上,專門為他提供了一個被稱為"信息辦公室"的特定空間,這實際上一個展示博伊于斯自己的行為藝術作品的殿堂。他展示的不是雕塑,而不過是他以自己的思想與所有的來訪者進行辯論。這可能是最大眾化的展覽形式。當問到他為什么要以這種方式把政治帶入一個藝術環境時,博伊于斯答道:"因為未來真正的政治意圖必定是藝術的。這意味著它們必須根據人的行為,根據人的政治自由來組織。"他在其他地方也采用了同樣的政治對話,一個有意思的傾向是利用博物館和畫廊來作為他的講壇。他在那兒掛一塊黑板,寫上他的公式,用以證明他那后來作為藝術作品固定和堅持下來的到處擴散的思想。
理查德·朗格、吉爾伯特和喬治及約瑟夫·博伊于斯的作品通常被藝術家本人和分析其藝術的那些人稱為"雕塑"。這無疑是因為他們都有在藝術院校受過專業雕塑訓練的背景--朗格與吉爾伯特和喬治都是畢業于倫敦的圣馬丁學院,這是一度由卡羅和他的追隨者所統治的學校,在英國人看來,他們是反對卡羅所領導的那個團體的教條的代表人物。通過把事物推進到極端,他們在普通觀眾的精神上,在他們對這個時代的藝術的感覺中制造了一場混亂。而當今明顯具有傳統特征的雕塑家向這些觀念藝術家的思想提出了挑戰,新一代雕塑家的行為被認為與博伊于斯等人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個人經歷所提供的背景是對立的。